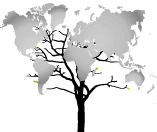郭愛華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絕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簡而言之,那時跟現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囂的權威堅持要用形容詞的最高級來描述,無論是其良善還是邪惡。 ”
當十九世紀的狄更斯在《雙城記》開篇中對他和他之前的時代做出如此洞察的時候,他也許已經知道,這樣的描述將同樣適合於多少年後的二十一世紀甚至以後更多的時期,因為“那時跟現在非常相像”。雖然二十一世紀似乎有很多新鮮事情,人口空前增長,科技迅猛發展,但是仔細品味起來,與人類生存狀態切實相關的根本問題其實都一如既往。
彷彿是對狄更斯比較廣義的洞見做一種具體的註解,台灣學者賴建國博士對當今時代做了這樣的觀察,“這是一個高科技低道德的時代,資訊爆炸人心空虛的時代,網際無邊人際疏離的時代,價值多元方向迷失的時代,威權解構自我錯亂的時代。”1 確實如此,人類不斷遞增的慾望正在超越地球的承受力,我們擁有的高科技也許足以摧毀整個地球;我們似乎擁有一切,而我們內心深處卻同時又有著一無所有的驚恐和無家可歸的焦慮,跟狄更斯時代和他們之前的人們都一模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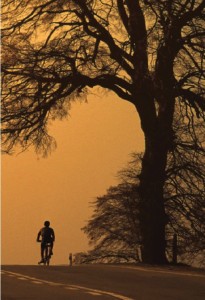 當現代人在自以為是的傲慢中鄙視貌似落後的過往時,卻無可奈何地發現自己每日都陷在與昔人一樣的困境之中,“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於是,在瘋狂地追求慾望的滿足時,又絕望地發現自己所孜孜以求的一切卻離自己越來越遠,甚至於最基本的情感需求都因為漫無止境的慾望而變得越來越難以滿足。結果,作為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我們一方面永遠都難以安靜在一個地方,永遠都在通過手上的某種高科技玩意兒把自己的觸角伸展到另一個地方;另一方面,我們又都非常想“家”,想念一個供應充足的星球、一個美好和諧的社會、一個生氣勃勃的事業、一個穩定充實的工作、一個溫馨歡樂的家庭,一個我們感到心有所歸的地方。然而,這一切在我們匆匆的行色中,卻一如鏡花水月,可求卻不可得。一百多年前狄更斯的洞察力真是穿越時空:“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當現代人在自以為是的傲慢中鄙視貌似落後的過往時,卻無可奈何地發現自己每日都陷在與昔人一樣的困境之中,“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於是,在瘋狂地追求慾望的滿足時,又絕望地發現自己所孜孜以求的一切卻離自己越來越遠,甚至於最基本的情感需求都因為漫無止境的慾望而變得越來越難以滿足。結果,作為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我們一方面永遠都難以安靜在一個地方,永遠都在通過手上的某種高科技玩意兒把自己的觸角伸展到另一個地方;另一方面,我們又都非常想“家”,想念一個供應充足的星球、一個美好和諧的社會、一個生氣勃勃的事業、一個穩定充實的工作、一個溫馨歡樂的家庭,一個我們感到心有所歸的地方。然而,這一切在我們匆匆的行色中,卻一如鏡花水月,可求卻不可得。一百多年前狄更斯的洞察力真是穿越時空:“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無家可歸?心靈的飢渴
在這馬不停蹄的奔跑之餘,我們需要安靜下來,思考一下,我們所想的“家”究竟是什麼?在哪裡?為什麼我們會飢渴慕想家?我們怎樣才能不必再“想家”?
家究竟是什麼?是什麼賦予一個地方家的感覺?
問過不少人,有人說得概括、抽像一點,家就是那麼一個空間,在那裡有愛,有伴侶,有安憩,有平安,有安全感。有人說得實在、具體一點,家就是一張舒適的床和一個只有自己知道怎麼用才服帖的枕頭;有人說得浪漫一點,家是一杯溫暖的咖啡或者香茶加上一本怡人的書和一把舒適的沙發;有人說得詩意一點,家是愛的港灣和可安息的水邊;還有人說得充滿活力,家就是有一個才德婦人加上一群活潑孩子……每個人對於家的具體設想各不相同,但是仔細分析起來,發現每個人在家裡尋找的都是同一種感覺:歸屬感。事實上,有關家的種種美好描述,如果不是屬於自己的,那麼無論多麼美好、舒適、浪漫、才德、活潑,都不會給你帶來家的感覺。
然而,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樣的設想也真的僅僅是設想而已。賴博士所概括的“高科技低道德,資訊爆炸人心空虛,網際無邊人際疏離,價值多元方向迷失,威權解構自我錯亂”的時代特徵,反映出人心最深處的一種飢渴,一種與生俱來的需求—被愛、被認可,以及由這種飢渴衍生出來的對人生目的的追尋、對人生中有意義的關係的搜求,無論是在工作中還是在家庭生活中。然而,在我們每日的生活中,這種心靈的飢渴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滿足呢?細算一 下,我們每日的時間是怎樣分配的?有多少時間是在工作?這工作的地方平常的感覺又是什麼?有多少時間是在家裡?在家的時間又有多少是有效的清醒時間?蓋洛普的一個統計發現我們絕大多數清醒的時間都是在辦公室裡,在工作場合。而多年以來,辦公室的常規環境是否認和忽略人的這種被愛被認可的需求的,因為人們以為商業運作的頭等大事是利潤。員工的心靈需求?那不但不在絕大多數企業的日程上,甚至還會引起很多管理者的嗤笑,因為,在辦公室環境中,“親密”、“相交”和“相愛”這樣的詞是陌生到令人猜疑、反感、甚至起雞皮疙瘩的。
然而,社會是由一個一個人組成的,而人天生就需要靠外來的營養來維持健康和成長。紐約時報最佳暢銷書作者、美國著名心理學博士Henry Cloud克勞德博士說,健康的食物供給我們身體所需要的營養,良好的關係滿足我們心靈的飢渴。我們都知道有毒食物的傷害,但是很少有人想到不健康的關係對心靈的殺傷力。
我們都知道要刻意去生產和購買健康食品,卻很少想到要刻意在自身和周圍營造健全而不只是“有用”的關係。為什麼現代人彷彿在任何環境下都不能安心,都沒有歸屬感?永遠都在用某種高科技玩意兒把觸角伸向別處?因為當個人最深刻的內心需求不斷在此處被否認和拒絕的時候,別處就變得特別的有吸引力。所以現代人的心靈無家可歸,常在浪跡天涯。所以整個社會就會展示出前面賴博士所歸納的時代特徵,也就是為什麼整個社會的創造力和幸福指數下降,因為沒有一個地方讓人有歸屬感。
企業是家? 零傷害文化
在人們每日花費大量時間的商界和職場上,最顯眼的事實是競爭,最常用的詞是“成功”、“盈利”、和“成本”。常常,企業對於員工的要求是最大程度上的績效,而有關員工的福利也僅限於物質上的獎勵。企業與員工之間的關係變成了相互的“有用, ”更直接一點地說就是相互的“利用”。當人們把自己絕大多數清醒時間都花在這樣的地方時,心靈的 飢渴自然就會成為最嚴重的疾病。我們已經看到過富士康的十三跳,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人需要心理治療,而更多的人則身處不健康的職場,默默地把上好的精力消耗在一些毫無產出的事情上……結果,員工和企業領導各有各的迷惑,當企業領導在為員工沒有忠誠度大傷腦筋時,員工卻在疑惑為什麼自己得不到足夠的重視?
有一種領導力的培訓叫做love and leadership,愛和領導力的培訓,尋求的是回歸到根本,回歸到愛中。如果在辦公室有愛,有關懷,有讓人內心深處的渴望得到滿足的文化,那麼人的那種被認可被接納的需求就能得到滿足,人的整體風貌也會得到更新,創造力和工作效率也會隨著內心的深度滿足而提升。企業的發展和個人的健康都將出現良性循環,並且進一步給社會的建造帶來良性的影響。
這種聚焦於人的理念始自現代管理學之父德魯克。“管理就是有關人的。”他說得非常簡潔明了。他的學生,曾經擔任美國財政部長的前美鋁公司總裁Paul O’Neil有一本已經捲了邊的筆記本。那是他50多年前做德魯克學生時的課堂筆記。筆記本的某頁記錄著這麼三個問題:
在你服務的機構裡:
1. 你每天遇到的每個人有沒有都讓你感到自己受尊重、有尊嚴?
2. 為了能夠對你的機構做出貢獻而需要的這些東西—教育、培訓、鼓勵和支持,你有沒有得到?
3. 有沒有人注意到你所做的事?
O’Neil這樣解釋他的管理方法,“對一個機構是否有卓越潛力的最有效檢測,就是看看該機構中的每一個員工是否都能夠毫不猶豫、毫無保留、不假思索地用同一個字來回答以上三個問題,那就是‘有’。”2 他在美鋁公司做總裁的時候提出的管理目標是,成為全世界第一個“零傷害”公司。他說,“如果我們珍惜每一個人、每一個同事,我們就會在工作中採用一些方法,使任何人都不會在工作中受到傷害。”
雖然有很多年,華爾街都沒有認識到人的價值觀、安全感與財富上的成功之間的邏輯關係,但是到2000年底,O’Neil 從美鋁退休的時候,公司盈利創下歷史紀錄,從1986年他接手的2.64億達到15億美金,公司市值更是增加了800%。這是德魯克管理理論現實應用的極好實例,正如德魯克自己所說,一個公司的價值就在於它的人,以及這些人的知識、能力和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如果公司的領導者能讓員工在辦公室感受到家的那種接納、關愛、看顧和讚賞,誰又會不想儘自己所能好好營造這個家呢?
船尾衝浪? 平衡的智慧
作為領導,在工作中又應當怎樣才能把企業建造成一個令員工有歸屬感的“家”呢?
克勞德博士在他的《品格》(Integrity) 一書中,形像地描述了這樣一幅管理圖畫—船尾衝浪(Wake boarding)。船尾衝浪的運動員藉著前行中的船後面的尾浪完成各種動作。如果船行駛得平穩,尾浪的兩邊就平穩和諧,衝浪的人就能最大程度完成動作,整體就有最佳的勝出機會。反之,如果舵手技術不佳或者不上心,尾浪就會變得劇烈多變,在後面衝浪的人就會摔個鼻青臉腫,整體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克勞德博士在他自己多年的管理諮詢生涯中見識過很多公司的“舵手”,也見識過不同的“尾浪”和整體表現。多年的觀察讓他得出這樣的結論,管理者在帶領他的部門或者整個公司的時候,他的後面也形成了一股尾浪。這股尾浪也同樣有兩條邊,一邊是任務(task),他完成了什麼?一邊是關係(relationship),他對身邊的員工做了什麼?在他們的心裡留下了什麼?這些員工能夠有最佳機會發揮他們的才能嗎?員工與領導、員工之間的互動帶來的是利益還是消耗?整體的表現就是他的部門或公司的真正業績。船尾的浪是“舵手”在公司裡留下的記錄。任務這邊的好壞直接反映在數字上,如果一塌糊塗,毫無績效可言,他肯定會被辭退,所以這一邊人們都知道要去做出最大的努力;而尾浪的另一邊,也就是人際關係的一邊,卻常常被忽視。但事實上,人們在與他人人生軌跡交會的時候必然在相互的生命裡留下自己的痕跡。作為領導,如果不能對追隨自己的員工有足夠的關懷和建造的話,即便在短時間內他的績效不錯,“尾浪”兩邊的不平衡也最終會帶來波瀾起伏,令後面“衝浪的”員工痛苦不堪,加重部門整體的內耗,並最終影響到“船”的整體航行。也就是說,在員工的生命中會留下問題、傷害甚至摧殘,並最終影響公司或部門的整體業績。
所以,一個好的領導者必須常常考量自己船後的那股“尾浪”是否平衡和諧,要在完成最佳數字業績的同時,建造良好的企業人文環境,而這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為促進的3。也只有當員工對自己的工作環境有一種歸屬感的時候,企業才能真正健康發展。所以領導者在帶領大家的時候不能一味只看前面,而要時常回頭看看跟隨者有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懷,是不是很有激情地又很自如地正在與他同行。
父親缺失 ? 歸家的盼望
如果說關愛在職場上是人心靈的營養,那麼在家庭中更是人呼吸的空氣,然而,現代人的婚姻和親子關係更是重災區。很多的所謂“成功人士”都在個人財富積累上業績飆升的同時,家庭這條“船” 卻傷痕累累,跟在他船尾衝浪的妻子兒女更是不勝其苦。社會在向他們的“成功”大聲喝彩的時候,常常忽略其背後一塌糊塗的家庭狀況。中國的離婚率每年急劇上升,從統計數字看,2010年每天有5300多對夫妻在辦理離婚手續,差不多是191萬對一年。
一向對數字不太敏感的我,有一天不經意間注意到身邊一個具體的現象,才真正有了觸目驚心的感受。大學時期同班有一個宿舍的8個同學中碩果僅存不曾離過婚的只剩下一個!我相信,每一對離婚的夫妻都在心靈的深處渴望著真愛,卻又在現實生活中面對無望破碎的關係而轉向別處。這就是現代婚姻家庭的弔詭,人們一邊極度地想家,一邊又不愛回自己的家,甚至身不由己地闖入別人的家,指望在那裡找到自己家中所缺失的愛和認可。對於現代的孩子們來說,恐怕最大的問題就是生活中父親的缺失,也許因為他太忙,也許因為他已經離棄了他們的家,也許因為他身在曹營心在漢,感情流落在他鄉。
在這樣的社會、工作和家庭環境中,現代人怎麼能不浮躁?這種浮躁正與人心靈深處對於被愛和被認可的渴望息息相關,正是某種程度上心靈想家的一種折射。所以,無論是真正意義上的領導力提升,還是職場的經營,或是家庭的建造都需要在根本上解決人們心靈“想家”這個終極的問題。 我們想家是因為我們不在家。
有一個家園,一直都存在。那裡有健全的自上而下的關係,也有健康的橫向的關係,因為在那裡有一條命令,“你們要彼此相愛。”在那裡,愛是恩典,也是盟約。想要不再“想家”,最徹底的辦法就是“歸家,”不只是把身體帶回家,而是“將心歸家,”接受那恩典的愛,堅守住愛的盟約,擔負起愛的責任來。只有當心靈歸家的時候, 我們才能擺正生活中所有的關係—無論是企業、職場還是家庭,也才能在健康的關係中汲取滋養心靈的養分,才能真正地有發自內心的平安和喜樂。每一個人都必須正視自己心靈深處的渴望,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只有在人生的一些終極的問題上拷問自己的心靈,回歸家園,才能在人生的一些現實的問題上將心歸家。我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我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那古老的智慧如是說。